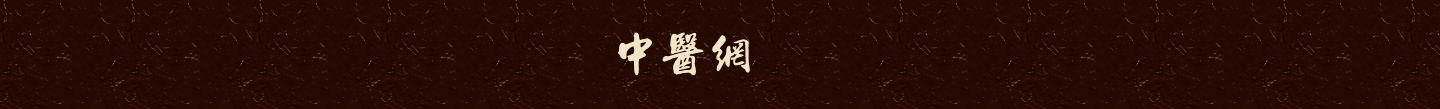藩国杨克黑暗时辰里的一场打坐
药膳食疗 2020年07月20日 浏览:2 次
戴潍娜
一个总写 好诗 的诗人并不稀奇,一个总写 烂诗 的诗人更是满国皆是。然而,一个诗人,若能一手写作学院派认可的知识分子性质的所谓 好诗 ,一首写出大众情人般妇孺皆喜的所谓 烂诗 ,则需兼有艰深曲高与兼济天下的心灵质地和社会担当。 必出世者方能入世,不则世源易堕;必入世者方能出世,不则空趣难持。 这样圆融通达的境界在当代诗人杨克身上获得了自在任性的表达。若是依照许多知识分子的偏见,李白那些流传最广的,诸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的作品,大约是其作品中最 烂 的垫底之作。大众的掌声是否对 好艺术 构成了玷污,这是个千古之辩。2015年杨克出版诗集《杨克的诗》,在没有媒体炒作的情况下,几番加印脱销,成为除北岛、余秀华之外最热卖的诗人。
我写关于世界的诗歌,将现代性锲入现实关怀,把个体生命融入时代语境,呈现特定生存空间的元素,同时坚信为人类写作。 这是杨克对诗歌创作的自我阐释,秉持这份情怀,他写出了《人民》《火车站》《天河城广场》等一系列从 当下的、日常的、具体的 生活场景入手,记录并评判时代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展现出作者一贯的,对于所处社会背景入木三分的刻画与批判。与一般写字的人不同,他反对那些沉迷于自我和书本上的理想、终极之爱,放大高蹈价值意义的虚弱知识分子,欣赏、钦佩在流放中不忘为矿工子弟办学校的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明白自己有和义务付出。
吊诡的是,这样一番浓烈的社会理想,坚毅的社会担当,连同其对大众的魅惑力,并没有妨碍杨克写出镜花水月般虚无艰深的学院派诗歌。《信札》大约就是虚无之中最虚无,内部技术最为无懈可击的高蹈之诗了。
杨克创作《信札》的时间是1995年7月,距今已逾20年。20多年里,文坛不乏对杨克诗歌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解读和评论,其中大多评述文章的关注点多在《我从现实和历史穿过 伊岭岩游感》(1982)、《走向花山(四首)》(1984)、《夏时制》(1989)、《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1994)、《杨克的当下状态》(1994)、《火车站》(1996)、《天河城广场》(1998)、《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2001)、《对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2002)、《几个和尚在珠海情侣路漫步》(200 )、《人民》(2004)、等作品上,而成篇幅、集中谈论《信札》的文章却不多见。
是当初的评论界没有追上创作者在审美上的跃进?还是由于文字太有魔性,一时难于言明?总之,《信札》是一首预言之诗和等待之诗。如今相隔二十年,许多预言已可怕的兑现。时间造就了更多比对物。一边看一边比,也就把一些谜团揭开了、问号拉直了。这是历史的悖论:我们努力还原历史真相,可实际上,在历史真相那里永远看不清真相。
《信札》开篇即有魔性的声音,一路奇景令人惊讶连连。读者的灵魂如被舔了一口,那种不由自主的亲昵带来的受难感,将整首诗牵引进第七度空间。在魔鬼之手面前,读者能做的只有 承受。 进入地狱的那一瞬,绝望涌来如同最初的爱情。 爱与痛在极致中相互转换,亦如真实存在与乱梦幻界两相颠倒。透过纸背而来的魅影是谁?且读这一句: 诸如语气、语调、有机无机的停顿/甚至你心里杂音的强弱。 这气息系动的是文字的生命力,它镜子一般,无比精准地反映出人们心里的光谱,以及时代的情感配比。气味会最先勾起回忆的幽灵和未来的幻影: 不可救药的气息,还有体味 /刹那的疼痛,躲在格子里写字的人/不小心就会被字走漏了风声。 此处,本诗幽暗的主人翁开始显现,字是一张脸,字亦是信使,诗是预言。在它们面前,诗人无处躲匿,开始无限解剖自己,诗人的多重人格对话开启。他嚎叫: 我在变俗却没人管我 ;他哀鸣: 觉得自己一寸一寸地死 ;他感慨: 许多人不如一只鸟儿/人,真不知是什么鸟 ;他又反驳自己: 别听我扯淡!我好像很有情绪 无端端地有什么情绪啊? 诗人深刻地刻画出了沉思中必有的无聊。
行至《信札》第三封,诗歌的历史性和预言性愈发分明。 如果没有你的字为证/鬼知道你是谁,鬼知道我在做什么, 可见,字是证言,字是预言。这首信札看似镜花水月,却真实勾连起了走不出的历史和走不进的未来,成为一首写在社会转型期的预言之诗。 垃圾。/我的周围。你的周围/ 于是你也是。于是我也是 ,被污染的命运被提前写就,在2000年以后才浮出水面的社会问题以及被技术文明垃圾化,被消费主义污染的一代人的命运,早早在诗歌里一语成谶。
抵达未来,须经由幻想之途,如诗人所言 呀,呀,或许这两种虚构都不对劲/可要男人停止幻想比不让一个女人照镜子还要难受。 在这些迂回的预言之中,诗人杨克成为了转型时代的一个制造镜子的人。这些虚幻的镜子同时隐藏陷阱。 我不认识你却又熟悉你,我无法验证你的存在 !因为,这里只有 你的字 ,而没有 你 。这种严密逻辑流露出的痴迷倾诉带点不依不饶,却也将诗中反复触及的一对矛盾自然呈现了出来:真实与幻象。其中存在大量的悖论空间,全诗结尾在这一主题上又进一步,一直推至逻辑和感觉的极限 只是我一直无法肯定这是经历过的事件还是愿望的幻象。 如此真实,却也这般虚幻。《红楼梦》中描写甄士隐在梦中来到 太虚幻境 ,看见 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的对联,可谓无意巧逢 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 的人世禅机。雪芹此番良苦用心道尽了天地人心、阴阳两界普遍存在的 真 与 幻 之内在奥秘。杨克的疑问正在于此,为什么当我们把真实的事物或感觉当作虚幻的事物或感觉时,那虚幻的事物或感觉竟然来得更加真实,反之亦然?此处的问题意识与庄子一拍即合:《齐物论》中记载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到底是庄周在梦中成为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成为了庄周?虚幻,可能是另一种更为有力的真实!
杨克曾经说 写诗,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 ,这印证了 人类用语言证实自己的存在 这一判断,也使维特根斯坦关于 语词的意义在于被使用 这一语言哲学的命题在诗歌领域得到具化。诗人写诗的过程,既是对幻象之真实的建构,也是对存在之真实的解构;既是对存在的百般剥离、质疑和拷问,也是对存在的进一步划界、确认和指证。《信札》中有这么一段: 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我觉得我已经在别的地方 。从 我觉得 在别的地方 的欲念和幻象,到 我觉得 在别的地方 的判断和确认,一念间瞬乎完成解构和建构。其中频频折射出杨克的存在哲学。读《信札》一诗,有时感到是在被诗人带着穿梭于真实和虚幻的迷宫之中,时而当下,时而过去或者未来;时而个人,时而家国乃至社会;时而现实,时而理想以及信仰,一路进行感觉和逻辑上的冒险。《信札》的情感由书信生发,给我们呈现的却不仅仅是 我 和 你 之间单向互通的心声倾诉,而是有一代人的生活感悟 , 我们/隔着漫天遍野的客观/忙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无根本无居所。现代人的状态。人类的状态 。
诗人在一个黑暗的时辰里进行了一场打坐与到目前为止只做团购这一件事情冥想,与日常生活出现一次有力的剥离,这剥离并非逃避,而是一种内在的反抗,就像木心所言 反抗,不是一静一动的反抗,而是从人的根本上,你要我毁灭,我不。
二十年过若能取胜第二轮遭遇塞尔比和伯内特的胜者去了,《信札》中折射的虚幻历史与未来,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真实。诗人都是预言家的后代。曼德尔施塔姗夫人曾写道: 诗人是与其诗作一同开始理解现实的,因为他们的诗中含有对未来的提前赞美。 二十年来,《信札》与诗人杨克一同生长,一同认真的赞美,认真的恐惧,认真的忧虑。
戴潍娜,青年诗人,作家。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杜克大学访问学者。文学博士。近年来高频率活跃于文坛诗会上,作品和评论文字见于各类媒体,其自成一格、反潮流的文风引发多方关注。小说诗歌刊载于《诗刊》、《星星》、《中国当代汉诗年鉴》、《青年作家》、《国家财经周刊》等杂志刊物。出版诗文集《瘦江南》、童话小说集《仙草姑娘》、诗集《面盾》等。翻译了多部作品,其中《天鹅绒监狱》2015年上了多种好书榜。
松原白癜病医院灰指甲传统治疗方法上海白癜风
- 上一篇: 藩国狂探第670章杀戮之心
- 下一篇 藩国br贪念真是一个奇怪的可怕的魔兽

-
孔蒂炮轰英超赛程欧冠成绩这么差心里没数吗
2020-07-10

-
鹈鹕油的功效与作用
2019-07-13

-
养眼护眼试试药膳
2019-07-07

-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概算56亿经费
2019-07-06

-
怎么吃核桃补脑效果好
2019-07-05

-
马蹄草的功效与作用
2019-07-01